任剑涛: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丨专访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60年前的今天,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
60年前的今天,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政治学者任剑涛的专访。
在政治学的许多同行看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的兴趣可能有些太“杂”:以伦理学思想史作为研究生涯起步,学术足迹遍及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比较,近些年又将目光聚焦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上。刚刚过去的2021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从政治学角度解读韩非子的作品。他对政治思想史的持续关注,在量化实证方法已大行其道的政治学领域也显得十分独特。
儒、法等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下中国的处境、“政治哲学”的身份问题、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任剑涛论文的选题风格往往视野宏大,体现出他们这一代学者的鲜明特点:研究起于极强的问题意识,善于打通不同知识的边界而不太拘泥于建制化的学科传统。而打通这些边界的线索,用任剑涛在此前采访中提到的话来说,正是“历史”,具体到他自己的研究,则是政治思想史。
任剑涛认为,回到思想史的脉络中,我们能够寻找到自己的研究与这些真正关键的“大问题”的联系,以一种更为立体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同时涵养我们的学术品味和“现实感”。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现实指向性的学科,政治学尤其需要避免米尔斯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在高度专业化的琐碎研究中远离政治现实。
而他也认为,尽管米尔斯对“宏大理论”有尖锐的批评,但却有着具体的语境。实际上,宏大理论对于我们立体、深入地理解真正的政治现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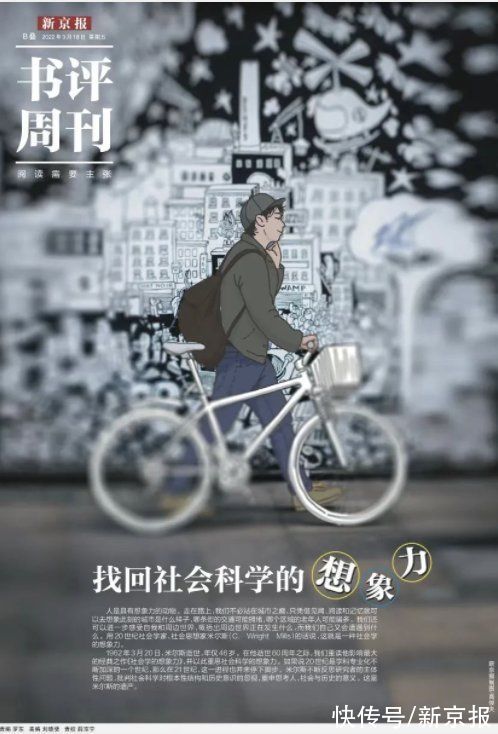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4。
「主题」B01丨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主题」B02-B03丨想象力及其问题
「主题」B04丨任剑涛 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
「主题」B05丨陈映芳 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
「主题」B06丨刘海龙 用学术想象力走出传播学的学科焦虑
「文学」B07丨中国式婚姻里,还有多少看不见的女人
「文学」B08丨与伊坂幸太郎一起写小说
不必教条式地理解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公共的政治哲学》《当经成为经典》等。
新京报: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局限在社会学学科内部,而是扩散至广义上的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你最开始接触到米尔斯是什么时候?初读他的作品获得了哪些启发?
任剑涛:米尔斯当下很有名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初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读完,当时还是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学的理论作品。随着我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久,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步溢出政治学专业范围之外,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了米尔斯这部书的重要性。他实际上在这本书中,是以社会学为一个窗口,来审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方法论意识。
作为政治学的学者,我对米尔斯的作品关注最多的其实是《权力精英》和《马克思主义者》两部书。尤其是后者,这本书我们国家翻译的也很及时,在米尔斯逝世前不久就印出来了,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米尔斯摘录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们的作品,另一部分是他对这些内容的评论。其中体现出米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是1978-1982年读的大学,当时社会学最主要学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后来马克斯·韦伯作品的传入,也几乎是塑造当时社会科学(不仅是社会学)思维的形态。而米尔斯深受韦伯和马克思的影响,但是他又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他们审视问题的方式。对于马克思,米尔斯不满意我们平时批判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即一种经济决定论。
而对于韦伯,米尔斯也与其进行了某种“隐匿的对话”,并提供了一种与韦伯很不一样的社会学论述。比如韦伯谈“价值中立”,也对时代和社会参与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这些和米尔斯是明显不同的。米尔斯恰恰强调研究者们要将自己的关怀融入时代环境,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学术研究,这对当时的我来说震动也很大。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 网址: http://www.llsyzzs.cn/zonghexinwen/2022/0323/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