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丨专访(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马克思主义者》,C.赖特.米尔斯 著,商务印书馆1965年7月。 新京报:关于理论的研究,你提到过多次需要有“宏大视野”,在这方面,米尔斯对“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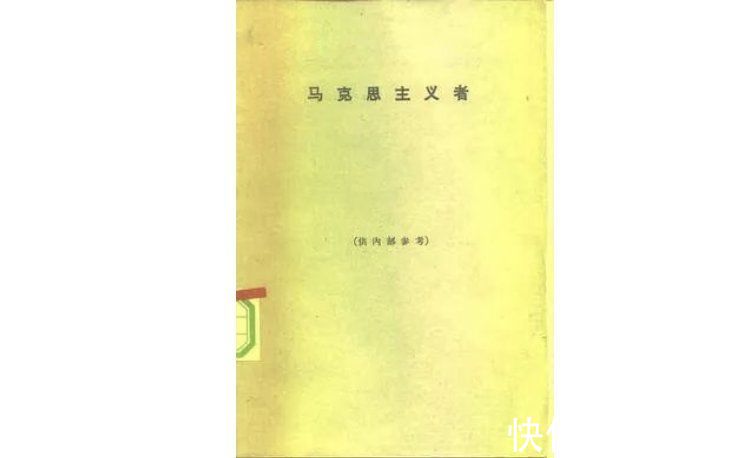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者》,C.赖特.米尔斯 著,商务印书馆1965年7月。
新京报:关于理论的研究,你提到过多次需要有“宏大视野”,在这方面,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取向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矛头指向的是社会学的帕森斯。就政治学研究来看,你又会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
任剑涛:我认为米尔斯主要指向的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存在的脱离社会而建立封闭知识共同体带来的种种弊端。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也经常被后代学者和学生们提起。这种对宏大理论的拒斥,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认同。客观地来说,米尔斯本人也有些忽视宏大理论的意义,他的几部作品,也比较遗憾地没有太多理论独创上的意义。如果是为了抨击一种时代的特定局限(学科的封闭化),而对宏大理论本身做太多的批评,就走得有点过头了。从我做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宏大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相当重要的路径,也是当下人们思考问题、做研究时缺乏的。我们不必教条式地理解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批评,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矛头特别指向的是帕森斯,帕森斯的理论是非常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而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论重视“结构”鲜明,关注“功能”有限,具有保守主义色彩,无力解释和预测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米尔斯炮轰的问题是很具体的。其实米尔斯在做社会学研究时,就明显受到宏大理论的影响,他自己就明确表示他所受的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倘若没有宏大理论的支撑,哪怕是他提倡的、可称为“中层理论”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到了晚年,米尔斯也在试着逐步提炼自己的“宏大理论”,他去世前编就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和他前期研究的问题取向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外,他一直致力于美国社会学理论的纠偏,其瞄准的对象丹尼尔·贝尔也有着很强的经验性,但也尝试建构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化问题。这是米尔斯与批评对象共享着宏大理论建构方法的表现。
总之,宏大理论和经验研究不可偏废。中国现在的政治学研究,乃至人文社科研究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可谓是“双输”的局面。尽管中国现在总在提要多做实证研究,但其实我经常说我们目前严格的实证研究不多,真正的“规范研究”甚少,重复劳动较多,理论创发罕见。这正是宏大理论与经验研究需要双突破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这和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是有关系的。中国社会学史家指出,《乡土中国》的问题类型接近学术散文,是从社会调查里得出的一些感悟,很好读,很启发人,但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系统的阐释。在这点上,费老的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的贡献反而更大。但他们的作品不那么好读,流行范围有限,没有费老发挥的社会学普及作用大。
我很尊敬费老,在研究中也得益于他著作的启发。这从我购置《费孝通全集》,以及声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受费老的“整篇零写”塑造,都可以印证。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从乡土中国到乡镇中国,再到城市化中国的研究,尽管有一个递进线索,像彼此间是相对孤立的,没有一以贯之的宏大社会理论建构将之串联起来。这是一个遗憾。这是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必须要补的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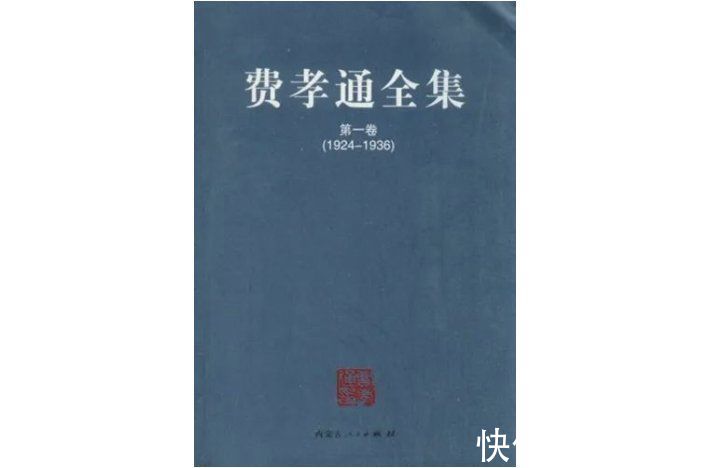
《费孝通全集》,费孝通 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思想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学术审美
新京报:你的研究兴趣发生过多次的转移,近些年的研究视野也非常广博,涉及到比较政治学、思想史、乃至新技术与政治(人工智能)的关系等。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研究兴趣变化的过程?最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任剑涛:概括地来说,我研究兴趣的变化和我所处职业的定位是密切联系的。我研究生在中山大学读的中国哲学史,1989年毕业后留在中大的德育教研室,这段时期基本上就是研究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结合了一下我的博士专业,具体主要是做伦理思想史。后来我调到政治系任教,从1993年开始在中山大学讲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思想史。200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已有老师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改教西方政治思想史。2016年我又调到清华大学,这门课又有人教了,我又改回教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以客观地来说,职业的多次调动,让我经常围绕当下任课的方向去组织我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其实还挺符合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里写的那种研究方法,做资料库,不断根据当下的情况来排序各种研究问题。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 网址: http://www.llsyzzs.cn/zonghexinwen/2022/0323/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