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丨专访(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就政治学来说,我觉得各种路径的思想史研究都有其价值。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种“知识还原”的研究。前者是从“文本”去
就政治学来说,我觉得各种路径的思想史研究都有其价值。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种“知识还原”的研究。前者是从“文本”去理解“隐微写作”背后的深意,但可能存在一些“以己度人”的问题。后者强调历史“语境”的还原,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纠正,然而可能弱化了思想家本身的主体性,似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只不过是受历史大势的牵引而已。
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语境”的尝试,可能也无法帮助我们把握更宏观的政治问题。所以剑桥学派最辉煌的成果比如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波考克写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些作品,基本都聚焦在现代早期的一个短程时间,比如14-16世纪。在这点上,施特劳斯学派反而可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对古典-现代关系做一个宏大的诠释。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奇怪,似乎本应由剑桥学派来呈现历史变化的节奏感与历史结构的变迁,而施特劳斯学派更多地去做一种“训诂”式的研究,但结果似乎恰恰相反。
关键的问题是,做这类有历史纵深感的政治研究,需要选择和个人兴奋点相契合的路径。同时最好能有当下的关怀,用我们正在面临的时代问题来确定我们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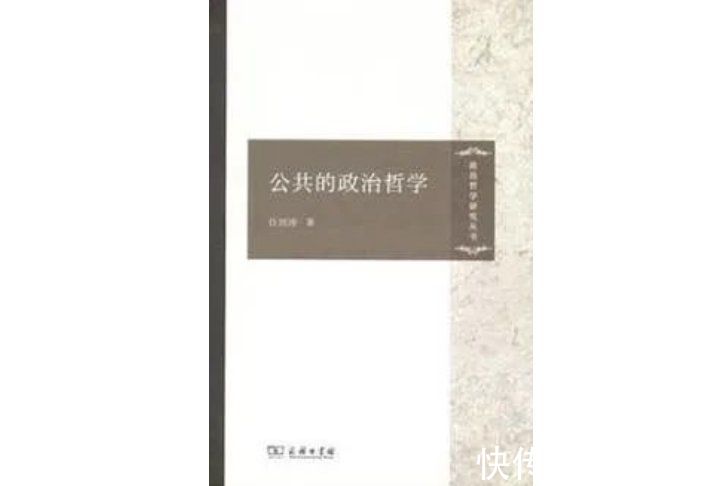
《公共的政治哲学》,任剑涛 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
看待政治思想切勿“价值先行”
新京报:写《政治:韩非四十讲》这本书,其中有怎样与当下切近的问题意识?
任剑涛:写韩非这本书是起于一个音频授课,起初本没有准备花很多精力,读相关材料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深究。虽然韩非有些说法听起来不太好,比如“用人如鬼”之类,但其中也有不少对政治本质的洞察,经常拿来和他作比较的西方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这个比较究竟有多大意义可以再讨论。但可以体现出韩非的重要性。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对韩非的批判,在我看来是不太站得住脚的。比如一个常见的看法是,中国近代转向民主和法治困难重重,韩非要负很大责任,韩非与法家哪里背得起这么沉重的责任。现代政治既然是经验世界的活动,中国政治能否实现“现代”转变,主要责任应在今人,而非古人。韩非当然不用对近代以来是否走出所谓的“秦政”负任何责任。更何况,他也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应该转变这种责怪的眼光,相对客观地看待韩非的文本。在他的年代,帝王术确实是当时政治首要的问题,国家要统一,到底是以军功爵、还是以血缘关系来建构社会和国家,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韩非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可以启发今人的相关思考。对他不必进行跨越千年的苛责,要他为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变负责。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今天的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切勿价值先行,用强烈的现代“移情”来衡量古代思想家得失,这会妨碍学术界潜心研究真问题,导致学术圈的“党同伐异”。
政治思想研究,不能以现代为唯一坐标。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古今之变”,尽管这种转变中间一定有连续性在。中国古代依血缘关系奠基的建国,便是“大型的小国”,没能创制现代英国那样的“小型的大国”,两者间具有显著差异。古代中国是“大型的小国”,指的是,虽然国家规模大、人口多,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社会组织规模并不大。像费孝通《乡土中国》里写的,“齿序结构”是个社会基本结构。这使得中国在社会生活中处理排序问题,就比西方简单不少,比如很多时候依年龄排序,同一场域的人群就容易认同。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小型的大国”,虽然人口不多,地方不大,但却创制出复杂的现代国家制度。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就需要适应这种剧烈的变化。比如我们不能幻想在现代的高度流动性社会,还能重回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建构,所以我对近些年重启“家国天下”的论述,一直都持批评的态度。我们不能脱离当代的现实,去一昧地“回到古代”,从经典中寻找医治现实问题的药方。这其实就会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经验脱节,陷入一种米尔斯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之中。
新京报:此前接受采访时,你曾提到最近在写作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三卷本,可否介绍一下这个写作计划?
任剑涛: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米尔斯曾提到最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能把个人的困惑和时代的结构性问题相关联。所以我写作的虽是思想史,但其实还是面向我个人的具体经验,也和我始终关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 网址: http://www.llsyzzs.cn/zonghexinwen/2022/0323/558.html